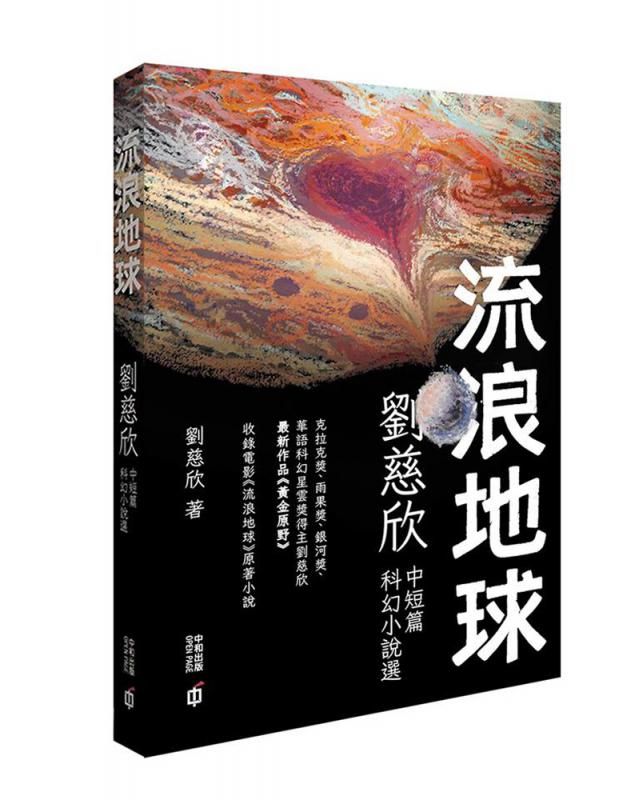
图:刘慈欣著《流浪地球──刘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说选》(香港中和出版,二○一九年)
刘慈欣生於一九六三年的山西,父亲曾在北京煤炭设计院工作,后来去到山西做煤矿工人。从小在矿山上长大的刘慈欣一直喜欢看西方科幻,少年时代深受以托尔斯泰、米哈伊尔.萧洛霍夫等作家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是以西方的哲学思维和科学观写科幻小说,在採访中亦表达过“我更愿意外国的读者看《三体》是因为它是一本科幻小说,而不是一本中国的科幻小说”的观点。在小说《流浪地球》问世之初,评论界曾一致认为这部小说中有很强的故土情怀和恋乡情节,对此刘慈欣最初并不认同,却随时间的增长最后坦然接受。
回望“伤痕” 展望未来
他在给另一部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探险队》的后记裏写过:“科幻是面向未来的文学,但当我们仔细研读众多的科幻作品,拂去其中那五光十色的技术幻影,从它们最基础的世界设定来揣摸作者的心境,竟发现科幻是很怀旧的”,他说《基地》是罗马帝国的翻版,《沙丘》是中东的王朝,太空中的宇宙飞船与大航海时代的帆船无疑……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很多年裏,刘慈欣似乎都在给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脱离小说光怪陆离的设定,背后是七十年代的乡土中国,是乌合之众的疯狂,是少数精英的死亡,是为了活着放弃人性:他的书裏有着明显的伤痕文学的痕迹。《乡村教师》中贫瘠的黄土高原,《地火》裏漆黑的矿区,《朝闻道》裏科学家们得到真理就要被毁灭。《三体》的故事的开端是在七十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叶文洁在目睹父亲惨死、一次次对人性感到失望后,回应了三体人发来的信号,背叛了人类,成为地球三体组织的最高领袖;而在之后对抗三体人的计劃中,领导人类的面壁者之一的雷迪亚兹死於人民愤怒的暴动。《流浪地球》中,随着地球在宇宙流浪的人们迟迟不见太阳的爆炸,在煽动下将“流浪地球计劃是联合政府为独裁统治出卖人类与地球”的谣言信以为真,组成叛军,处决了联合政府五千位计劃制定实施者。
而他在科幻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待科学的态度其实并不太主流。科幻若想跻身严肃文学,必然要有对人与自然和人与技术的思考。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当前“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中,人们越来越警惕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资本借助技术疯狂逐利所遭的反噬,技术对人性的影响和人主体地位的取代等等。因此主流的科幻常常带有反科学的倾向,比如最有名的《2001太空漫遊》中,作者克拉克通过对人工智能哈儿脱离人的掌控,甚至可能对人进行反扑的描绘,对於先进科技及其中危险性进行探究。而刘慈欣在作品中却很少谈及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在技术对人进行思想控制这个话题上说过:“技术的邪恶与否,要看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什麼。如果人类的最终目的不是保持人性,而是繁衍下去,那麼思想控制就不是邪恶的。”
他称自己是“一个极端技术狂热者,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其小说《地火》中,他用前面大段的篇幅勾勒了两代人为煤矿开採工作付出的沉重代价,草木湮灭、生灵涂炭,最后将时间转向一百二十年后,当气化煤早已普及应用,那时的孩子回望这段历史感慨: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这之中不难感受到其以时间与科技的发展,消弭当下的困顿,书中表现出的不仅是对於技术的极度崇拜,也是对当前道德的迷茫与虚无。刘慈欣本人亦多次表示认为人性的概念模糊,“从原始时代到现在我找不到人性中亙古不变的东西。”他举过一个古代围城之战的例子:“食物匮乏,一个将军把他的妃子杀掉分给士兵吃,这个在当时也是一种道德,甚至是牺牲精神的美谈,而现在人根本没办法理解这种恐怖的道德。如果一万年之后人类还存在的话,那时候的道德说不定比现在看上去更恐怖。”如上观点,我们可以在《流浪地球》中看到,包括平静刻画了末世中主人公父亲的出轨与母亲的无动於衷,因为生死存亡之际的人们,对逃生的慾望压倒了一切,爱情变成无关紧要、不可理解的东西;他描绘了那时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古代人类在救父还是救子之间两难的行为,先幼后长成为普世值,岩浆渗入地下城后所有人按照年纪从小到老的顺序进行逃亡,最终主人公的母亲没能逃出那次灾难。书中所有的人物在生死面前都表现出近乎机械的“听话”与“理性”,无所谓善与恶。对於这当中透露出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冷酷,他说:“我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冷静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读者认同了我的这种选择。”
放下人性 笃信科学
对道德今天面对的难题无动於衷,也对道德今后的堕落不以为然,刘慈欣对人性的虚无,和对科学的笃信,让人怀疑他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家是否真的具有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包括怀疑精神,包括反思精神,却独独不包括对科学的无限崇拜精神。
十二年前,在成都举办“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期间,他曾引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刘慈欣该是康德义务主义的拥趸,康德义务主义将伦理诉诸责任,而非感情的结果。在那场大会期间,他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之间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刘慈欣在现场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当人类世界只剩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他与江晓原必须吃了第三人才能活下去,吃还是不吃?江晓原的回答是不吃。刘慈欣说:“可是宇宙的全部文明都集中在咱两个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淹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现在选择不人性,而在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江晓原说:“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於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了。”
刘慈欣在小说中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人类被扔进末日般的困境中,在“人性还是生命”的问题上,放下人性的偏执,选择活着。比如他在《三体》裏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则:“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以此来阐释他基於生存与鬥争的宇宙社会学;又比如在《流浪地球》中规定地下城只能容纳三十亿人,地球上的六十亿人必须以抽籤的方式决定去留,并规定资格不得转让、赠与。
上周荷里活导演占士金马伦(James Cameron)与刘慈欣进行了一场对话,金马伦告诉刘慈欣他希望看到一些乐观的东西。的确,刘慈欣的书有一种极为压抑的底色。他强烈的求生慾望和对人类永生的慾望,让他的书中没有“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只有生存、生存、生存。他以社会达尔文的方式对抗末日,所认为的“希望”,是“人类在极端困境到来之际,文明为了生存下去,如何摆脱道德的羁绊”。但如果科幻小说既没有对人机关係的反思,也没有对人类命运的自省,恐怕让人困惑:剩下的理性究竟是理性还是麻木,所谓的生存是为了人类还是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