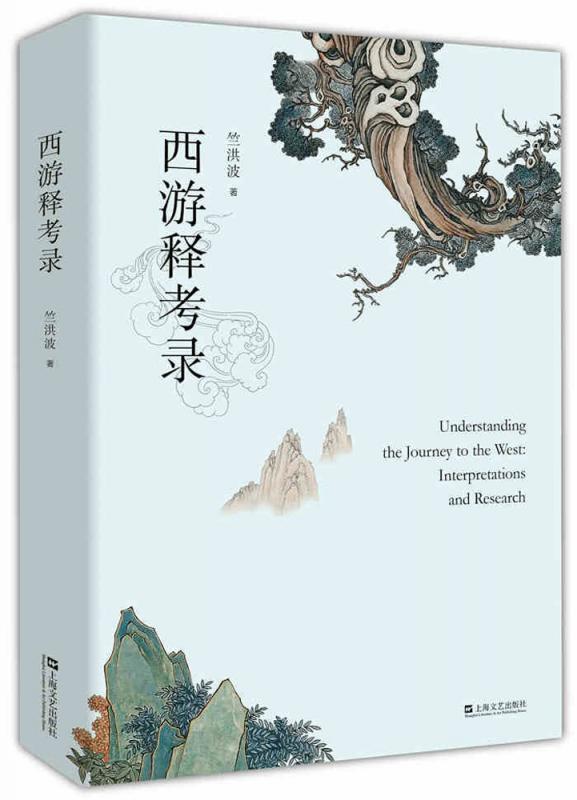
图:竺洪波著《西遊释考录》,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一六年
《西遊记》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提起《西遊记》,你会想起谁?有人会说唐僧、孙悟空。有人会说六小龄童。还有人可能会提起“星爷”大名。不过,在《西遊记》研究学界,大家会想到竺洪波,也就是《西遊释考录》的作者。竺洪波矢志西遊研究多年,曾出版内地首部《西遊记》学术史专著《四百年<西遊记>学术史》。这本《西遊释考录》是他设想中的“西遊三书”之二。该书从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美学本体和现代史论四个维度,进行文本阐释和深层解读。\胡一峰
《西遊记》成书研究始於“五四”时期,而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西遊记》研究,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在“五四”之前,“证道”与“谈禅”构成了解读西遊的两大範式。“证道”的潮流开启於清初刊刻的《西遊证道书》,“谈禅”则以《西遊真诠》为代表。佛道之争,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而在《西遊记》中,也确有不少反映佛道论争的描写。比如,唐三藏在比丘国与妖道论辩、在车迟国与妖道鬥禅,再如孙悟空与虎力、鹿力、羊力三位“神仙”鬥法,皆是隐喻佛道之争的经典场面。崇佛抑道则是《西遊记》的基本宗教倾向,取经路上几乎没有好道士,妖怪爱幻化的也是道士,相反,佛法尊严却得到了大大弘扬。这场论争孰是孰非,暂且抛开,但从宗教纷争角度解读《西遊记》,对於深入阅读这本名著并不妥帖。
“五四”时期,鲁迅和胡适携手论定《西遊记》的作者为吴承恩,推翻了《西遊记》作者为邱处机的说法。邱处机所作《长春真人西遊记》所记为雪山西行遊记,与演义小说《西遊记》并非一书。同时,他们又鈎沉史料,搜寻出了吴承恩著《西遊记》的不少证据。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西遊记研究的现代学术潮流,开了西遊记学术史之新风。在本书中,竺洪波归纳了“五四”以来《西遊记》研究的主要範式。其中包括,王国维的文献整理、郑振铎对版本演化的排序、孙楷第的版本考订、陈寅恪从佛经中考出《西遊记》人物原型、赵景深的民俗学研究,以及刘修业对吴承恩的研究等,正是诸位前贤从不同侧面和视角的开创之功,令西遊记研究虽不及“红学”兴盛,但也已敷衍成学、蔚为大观。
慧眼看透“西遊”IP
今天,“西遊”无疑已是个大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竺洪波这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其旨趣没有囿於象牙塔,而是从文化的广角视野,对影视乃至网络文艺中的《西遊记》也作了一番有价值的点评。他高度肯定了央视一九八六年版本的《西遊记》,以及六小龄童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又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纪中版本的《西遊记》特效失真、剧情乖谬,尤其是孙悟空这一角色演绎过於逊色,偏离了《西遊记》的原著精神。
更重要的是,竺洪波没有迴避近年来出现的恶搞西遊记等文化现象。他既对其庸俗化的欣赏趣味和不健康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批评,更深刻地指出,恶搞版西遊记“对原著的消解、颠覆作用只发生在大众消费的娱乐性层面上,对作品的哲理、宗教、社会文化等广袤、深邃的思想蕴藉基本没有涉及,也即没有指向作品文化精神的硬核:所谓‘感官盛宴’的表面热闹遮盖不住思想的贫乏。你别看他们表面上把《西遊记》搞得面目全非,但实际上并非伤筋动骨,只是情节上的改编、解构而已。对於《西遊记》主题和艺术精神的阐释,还是要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来进行。”而且,他还提出,所谓对《西遊记》的颠覆、消解,其实都没有挣脱开原著庞大张力的笼罩,“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应该说,这些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它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理性清醒、文化宽容和学术自信。尤其是在这个网络文化的时代,文化欣赏者正在变成创作者。三国、红楼等大IP也经历着和西遊类似的命运。竺洪波的观点不仅对於理解伴随着《西遊记》而起的文化现象有助,对於如何理解经典及其在“传播—接受”中的变异也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覆”之论添“悦读”之趣
《西遊释考录》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扎实基础上的,但竺洪波又独出己见,新说迭出,读其书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书中对《西遊记》这部小说本身,以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都有独到的解读,不乏“发覆”之论,引导我们把目光投向这部看似已十分熟悉的小说中那些不太熟悉的地方,平添了许多阅读和思考的乐趣。
比如,关於《西遊记》的主题,向来说法颇多。林庚认为这部书是“童话的天真世界”,而竺洪波把《西遊记》的主题解释为“自由”,提出“《西遊记》是一部表现中国古代人民追求自由文明理想的作品,哲理和审美意义上的自由(和谐)即是作品的主题”。在这一主题确认下,西遊故事容有了新的内涵,猴王求道是“生命自由的象征”,太宗入冥是“精神苦难的解脱”,如来造经则是“对社会和谐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自由主题的提出,使《西遊记》的诠释得以超脱於劝学、谈禅、讲道乃至阶级鬥争之外,多了一份解读的自由。
关於唐僧的解读也是如此。唐僧的形象,相信在大多数《西遊记》的读者心中并无高明,甚至被郭沫若贬为“愚氓”。在《大话西遊》等解构性作品中,唐僧更成了一个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可笑形象。如竺洪波所言:“世人读《西遊》,皆以行者为大英雄。”但是,他犀利地指出《西遊记》的母题是“唐僧取经”。这是全部故事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架构,其余的一切都围绕它而展开。“西天取经的主角毕竟是一位唐代高僧,而不是一隻通灵的心猿。……孙悟空和猪八戒、沙和尚一样,都是作为唐僧的补充被逐渐添加上去的,他们只有本领和作用的差别,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没有孙悟空,仍是帅旗不倒,尚能成‘西遊’故事;倘或缺唐僧,则如釜底抽薪,根本无以言‘西遊’了。”
竺洪波进而指出,借由唐僧这一艺术形象,小说表现了一种高贵伟大的精神品格,他将之称为“唐僧精神”,其核心是慈悲施善的胸怀。此外,还有坚定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唐僧看似文弱,面对妖怪毫无招架之力,却从内心深处显示出一种虽九死而不悔,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极富崇高感。当他接受取经的使命时,有人提醒西天路远,且多有虎豹妖魔,恐怕有去无回。但唐僧说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竺洪波讚叹道:“不畏生死的牺牲精神和崇高感,才是唐僧性格的主流,也是唐僧精神的基本价值体现。”而且,这种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崇高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审美,是唐僧独有的。我们读《西遊记》,可能被孙悟空的童心所打动,但深读之后则可能因唐僧强大的内心而感动。
书中类似洞见还有不少,比如,对西遊记中的自然景观描写的分析,提醒读者这些文字除了衬托取经路上艰辛的功能意义之外,还具有独立的审美欣赏价值。明瞭此层后再读《西遊记》,想来会别有兴致。
当然,书中还有些极有学术价值的点,似还缺乏足够的展开。比如,“吃唐僧肉”是书中最著名的“哏”之一,如白骨精所言:“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竺洪波提出,它构成了《西遊记》审醜描写的基本架构,如比丘国国王为治病而以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为藥引,再如玉皇昏聩、老君迂腐、如来耍奸等,都可视为“《西遊记》的另一种美学”。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由此申发开去,或可以书中那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妖精为对象,写成一篇大文章,可惜书中失之简略,让人有些遗憾。
中西会通与互释
《西遊记》是一本“西天取经”的书,其故事母体蕴含着文化交流的内涵。有意思的是,竺洪波释考此书也寄寓了中西对话的视角。在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要别求新声於异邦,运用“他者性”视角进行解读,借用西方文论的新术语、新观点、新方法,为《西遊记》研究开闢新时阈,注入新动力,取得新突破。被用来作为“工具”的西方文论理论或观点很多,比如克里斯特娃和罗兰.巴特的互文性理论、席勒以及人类学的“遊戏”理论、朗西埃的“文学─政治”学说等。
其中,借用巴赫金狂欢学说所作的解读尤为精彩。巴赫金用“脱冕”和“加冕”这两种狂欢节的仪式,来说明文学正统与草根、高雅与低俗的互换关係。竺洪波认为,孙悟空对正统秩序的反抗首先表现为“脱冕”,剥去其伪装,撕破其尊严,甚至将其打出原形。无论是三界主宰玉皇大帝、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道貌岸然的太上老君,在孙悟空的棒下和口中,都斯文扫地,是为“脱冕”;而孙悟空这个无父无母的石猴,却建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最终功德圆满,被封为“鬥战胜佛”,与唐僧平起平坐,完成了“加冕”。这一“脱冕─加冕”的深层结构,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充分地表达了小说中的反抗哲学。
《红楼梦》早已成学,近年来随着文化开明,《金瓶梅》的学术研究也渐次推开,隐隐也有成“学”之势。竺洪波在书中则提出了“西遊学”的概念,旨在以《西遊记》作为“文化底本”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全景式深度透析。从“后记”中我们知道,在竺洪波的写作计劃中,还有一部《〈西遊记〉学术形态学》,应该是构筑“西遊学”大厦之奠基之作,不免让人充满期待。